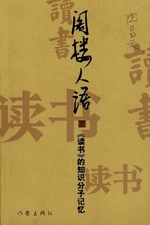 《阁楼人语》其实更像是一部“旧”书,因为书中大部分文字事实上已成为一些读者尤其中年读者过往十余年阅读生活中的一部分。据闻,在做《读书》杂志“主持人”期
《阁楼人语》其实更像是一部“旧”书,因为书中大部分文字事实上已成为一些读者尤其中年读者过往十余年阅读生活中的一部分。据闻,在做《读书》杂志“主持人”期
沈的文字独树一帜。而这个类似“操行评语”的现成语由于过于现成,因此需格外限制或规矩――他抱怨:不仅订数下降、纸张涨价、刊物拖期、错别字陡增自然都在抱怨之列,可令人诧异的是,甚至就连“整整二百个月份,月月在‘是’、‘非’中翻筋斗,讨生活。寻是生非,习非为是,以是为非,非中见是,今是昨非,彼是此非,是是非非,非非是是(第275页)”也在沈的抱怨主题之下。而有了这后一个“抱怨”,一个思想评论杂志主持人的尴尬与窘态、慧眼与鬼马也便被和盘托出;他表扬:不仅樊纲、盛斌、郭小平、赵一凡、申慧辉、吴岳添、周启超、刘承军、葛兆光、吴方、陈平原、夏晓虹、胡晓明、徐建融等一干思想才俊尽在其千字文中被隆重赞扬(第178页),甚至就连远在澳大利亚的学者桑晔先生附函称用自己应得的稿费为那些无力长年订阅读书杂志的读者订阅《读书》杂志,也会赢得沈之“悲欣交集”(第176页)……所以,用诸如文化雅量或编辑襟怀之类,确难包容下如是作为。我真正想知道其实是,在“沈昌文”-“总经理”-“主持人”-“社会活动家”-“饭局张罗者”等繁多身份间,其最本质的社会角色究竟何为?
如你所知,沈是一个爱热闹的人。每次见面,除去翻看他那个记满京城数百家特色菜馆电话号码的“PDA”外,就是聆听他口无遮拦的太多格言隽语――而那所有格言隽语,无不以牢骚怪话放浪自贬格式喷薄而出。沈最著名的一个口号被称之为“十六字令”,其中“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云云不仅广为圈内男男女女耳熟能详,而且颇合后来他自制标签所谓“不良老年”之定义。但其实,如此“玩笑”最需仔细揣摩认真打量――而当我将“情爱”云云置换为对学者耕耘的知会,将“情报”云云置换为对文化生态的预报,将“盗窃”云云置换为对学术资源的整合后,忽然发现,沈最恰切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思想经纪人”。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最初想起来大大不恭的“冒犯”却被我自己越想越真切。笼罩其中,沈的恁多“抱怨”或“表扬”竟一一演变为一个思想经营者的“市场”策略:它貌似嬉皮笑脸,但内藏诚恳;它确乎玩世不恭,可其实行端坐正谨严不苟。关于《阁楼人语》的评论其实已是多多复多多,但提示沈之所为“雅痞风致”与“慧眼仁心”其实互为表里相互牵动者,尚不多。
如此这般,文首劈头盖脸《阁楼人语》其实更像“旧书”云云,其实已无冒昧之虞,而全为真切褒奖――因为毕竟说,在我们这个年出书超过十万种、日出书超过八百种的国度,“新”比“旧”其实是一个更冒险的评价。而且,尤其当我们将《阁楼人语》一书中的恁多闲言碎语唠唠叨叨换位为“当代学术思潮史索引”或“中国当代思想广告史”等视角去解读时,一个更大的“发现”也便轰然呈现:学者专家难道不需要广告吗?思想学术难道不需要推介吗?而面对如此提问小心翼翼揣摩之余,也就发现,事实上能像沈那样与专家学者思想新锐吃川菜、品新茶、谈爱情,然后据此审时度势大力鼓噪之赞美之传播之弘扬之的人在全中国又有几个?所以我说,沈其实稀罕而外,也是无可替代。截止2004年,沈已年届七旬。我个人感受是,这位德高望重的“不良老年”整日价风尘仆仆从饭局到饭局,不是在咖啡馆就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所为无非是传播新进提携才俊。他整个心肠乃至于《阁楼人语》中且坏且怪且酸且甜东拉西扯的平白文字都如空气般围绕着我们,它实在比我们想象的珍贵更有甚之――因为“空气”我们虽然感觉不到,可却无时可离。
(《阁楼人语》,沈昌文著,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11月版,22.00元)
